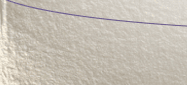概述我這一生中地球上的變化
我生活於兩個世紀之交,彷彿在兩條河流的匯合處;我栽進翻騰渾濁的水中,遺憾地遠離我出生的舊岸,懷著希望向一個未知的岸游去。
我們古老的風俗中有一個說法:我從床上能看見天空了 (1) ,從那時起,全部的地理都變了。如果我比較兩個地球,一個是我生命之始的地球,一個是我生命之終的地球,那我就都認不出來了。陸地的第五個部分,澳大利亞,已經被發現,並且住上了人:第六塊大陸也在南極的冰海中被法國的帆船望見,帕里、羅斯、富蘭克林等人也已繞北極的海岸航行一周,畫出了美洲的北緣;非洲開放了它神祕的孤獨;總之,我們的家園現在已沒有一個角落還不被人知。人們學習地球上所有使世界分離的語言;人們大概會很快看到船隻通過巴拿馬地峽和蘇伊士地峽。
歷史也在時間的深處做出重大的發現,神聖的語言已讓人讀出它們湮沒失傳的語彙,商博良 (2) 在麥茲拉依姆的花崗岩上破譯了象形文字,這些象形文字彷彿蓋在沙漠嘴唇上的封籤,回應著它們永恆的審慎……。
船舶借助剛剛逝去的運動,不再局限於河上航行,穿越了大洋;距離縮短了;不再有急流,季風轉換期,逆風,封鎖,關閉的港口,從這些工業傳奇到普朗庫埃的茅草屋,距離何其遙遠:那時候,女人們在家裡玩牌;農婦們紡麻織她們的衣裳;昏暗的樹脂蠟燭照耀著鄉村的夜晚;化學根本沒有顯示出它的奇蹟;機器也沒有使所有的水流和鐵器動起來織毛線和繡絲綢;煤氣還是個轉瞬即逝的東西,根本不曾向我們的劇場和街道提供光明。
這些變化並未局限於我們的日常應用:人類出於追求永生的本能,將其智力向上伸展:他在上蒼每走一步,都承認了難以言明的力量的奇蹟。那顆星,我們的父輩看來簡單,我們看來卻兩倍三倍地複雜;陽光置於陽光的前面,就產生陰影,並且沒有空間容納其擴大。在無限的中央,天主看著這些壯麗的行列在他周圍行進,這在最高存在的證據之上又增添了證據。我們用父親家裡的那兩盞燈
(3) 換取這些奇妙的東西。
讓我們想像一下吧,根據變得強大的科學,我們這顆羸弱的行星游動在一個以陽光為波浪的海洋中,游動在這條銀河之中,這條銀河乃光的原材料,是造物主使之成形的萬物的熔化了的金屬。某星的距離如此神奇,其光到達望著它的眼睛之時,此星已經死滅,光源死滅於光線之前。人在其活動的原子中何等渺小,然而他作為智力又是何等偉大!他知道星辰的表面什麼時候蒙上陰影,彗星數千年之後於哪個鐘點返回,而他的生命僅為一瞬!他是天之袍的皺褶裡一個看不見的微小蟲子,然而星球在太空深處的每一步都瞞不過他。我們剛剛發現了這些星辰,那麼,它們將照亮什麼樣的命運?這些星辰的發現和人類的某個新階段有聯繫嗎?你們會知道的,將要誕生的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退下。由於我的異乎尋常的高齡,我的紀念碑完成了。這對我是很大的寬慰;我覺得有人推我;我在船上訂了座位,船老大通知我一會兒就要上船了。倘若我曾經是羅馬的主人,我就要像蘇拉
(4) 那樣說,我在我的死亡的前夕寫完了我的《回憶錄》;但是我不會像他那樣用這樣的句子結束敘述:「我在夢中看見了我的一個孩子,他指給我看他的母親梅黛拉,鼓勵我到永恆幸福的懷抱裡享受休息。」即便我曾經是蘇拉,榮耀也永遠不能帶給我休息和幸福。
新的風暴即將形成,人們相信預感到了災難,更甚於我們曾經飽嘗過的痛苦;為了重返戰場,人們已經考慮重新裹上舊日的傷口。然而我不認為不幸會在近期發生:民眾和國王都已精疲力盡;意外的災禍不會猛撲在法國身上,在我身後發生的事情不過是全面變革的後果而已。無疑,人們將觸及一些令人難以忍受的視靜止
(5) 現象;世界不會沒有痛苦就改變面貌(它必須改變)。但是,再來一下,並不就是另外的革命;那將是大革命趨向結束。明天的景象已與我無關;它呼喚著別的畫家:該你們了,先生們。
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寫下這最後的話,我的窗子開著,朝西對著外國使團的花園:現在是早晨六點鐘;我看見蒼白的、顯得很大的月亮;它正俯身向著殘老軍人院的尖頂,那尖頂在東方初現的金色陽光中隱約可見:彷彿舊世界正在結束,新世界正在開始。我看得見晨曦的反光,然而我看不見太陽升起了。我還能做的只是在我的墓坑旁坐下,然後勇敢地下去,手持附耶穌像的十字架,走向永恆。
1 意思是人降生。 (回到段落)
2 法國埃及學家和語言學家(1790-1832),曾主要依據羅塞達碑譯解埃及象形文字。 (回到段落)
3 指太陽和月亮。 (回到段落)
4 古羅馬軍事統帥、獨裁者。 (回到段落)
5 天文學術語。
‧試讀‧我在巴黎的孤獨生活‧橫越大西洋‧概述我這一生中地球上的變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