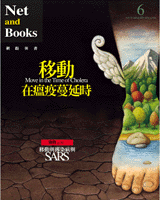|
如果六年後可以不必再為一個問題而困惑
郝明義
1997年四月的一個半夜,我守在電視機前。
前一天晚上,陳進興闖進了南非武官的家裡,挾持了人質,和團團包圍的軍警對持。在電視媒體的實況轉播下,現場的氣氛隨著槍聲隨著軍警的移動節節升高,然後高潮出現在一家電視台的主播把電話打進了南非武官的家裡,直接和陳進興對上了話,電視台成了全國收視的核心,陳進興的聲音也直接進入了每一台電視機前的家庭。
那場對話很長,對於其他只能播播屋外畫面的電視台相當於凌遲。因而電話一掛斷之後,其他一家又一家的電視台搶著打電話進去,繼續和陳進興展開對談。
電視上,訪問的主播有人一口一個您地稱呼陳進興,有人像是在訪問一個落難的江湖英雄,有人熱乎地套交情,希望陳進興同意他能親自進去當面專訪。而陳進興則侃侃而談,不是把責任推給死去的同夥,就是責怪白冰冰不肯快速拿錢來贖女兒的不是。殘無人性地折磨一個少女,再讓她葬身水溝裡的匪徒,似乎和他無關。那天最後到天亮的時候,陳進興近乎予取予求地拿到他一切的條件,走出了屋子。電視屏幕上,所有的軍警、幹探、律師,其實都只是配角。
從我自己的身邊,可以感受到,就從第二天起,原來當白曉燕屍體打撈上來的時候,台灣社會鬱積到最高點的恐怖與憤怒,一起消失了。我聽不到麵攤老闆再咬牙切齒地罵陳進興不是人,甚至,間或,我可以聽到一些覺得陳進興是個英雄的聲音。就算不這麼認為的人,也不覺得有正義舒張,或是危機解除的舒脫,有的,頂多只能說是洩氣。
那一個晚上,並不只是一場警匪對峙,以及對峙之後的反高潮,而是整個台灣社會參予了的一場危機處理。而這場危機處理,對接下來台灣社會的是非、價值觀的改變,影響極大。我不是社會學家,也沒有研究數字可以佐證,但我相信,那個影響是極不好的。
而不論是那天晚上當我看到第一個記者開始訪問陳進興的時候,還是後來很長一段時間,直到今天想起來的時候,我一直有一個困惑不解。那就是當一個脅持案發生(更何況這還是加上白曉燕案的脅持案)的時候,為什麼我們社會沒有一個應變的機制?台灣上演的美國電影是很多的,隨便看過一兩部美國警匪電影的人,不是都該知道碰上這樣的事情,首先就是要中斷裡外的一切聯絡,設定一個專線,由談判專家來集中對付歹徒,再視情況來誘導他投降,或是予以格斃嗎?
為什麼我們的電視台可以打電話進去?為什麼我們的執法單位不基於匪徒可能趁機為自己開脫或是扭曲真相,而切斷電話?我們包圍在外的重重軍警,為什麼沒有拿出他們該有的專業素養,以及標準作業程序來採取行動?為什麼最後甚至成了政治人物進去和匪徒談判,以致於造成後來許多爭議?
如果那天夜裡是由專業的機制和程序來處理,後來很多事情,又會如何發展?
多年來,我一直忘不了這些問題。
◎
2003年四月,白曉燕案滿六週年不久,台灣爆發了SARS危機。從早期的防疫有成,到逐漸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說是我們又碰上一次社會危機,應該沒有人會反對。
我不由得想起六年前的事情。
這次的危機,尤其在和平醫院事件之後,有許多相似之處。一處處隔離──只不過包圍在外的主角不是軍警;到處的電視實況轉播──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地取得爆料新聞;社會上被激起的恐怖和憤怒──只是波及的民眾範圍更廣,失控的程度更大。以及,等一下還要談的另一個問題。
不同的是:這次我們面對的,不再是一群匪徒,而是無聲無息,任何人都可能遭到波及,後果不可逆料的傳染病。
因而,在防疫還在進行的過程中,有一個本來實在不該評論,但是又實在覺得刻不容緩的一個問題:作業機制和作業標準程序出了問題的現象。這個問題的嚴重,可能凌駕一些我們目前呈現的問題與不足之上。
這些問題,在李家同先生五月六日的一篇文章中說明得很清楚:
在我看來,政府目前的管理制度,至少有以下幾個嚴重的缺點:
(1)沒有一個跨部會而又有地方政府代表的總指揮中心。
(2)沒有建立管理情報系統(Management inf ormation system)。
(3)沒有鉅細靡遺的標準作業程序。
他進而說明:
和SARS作戰,不僅僅是衛生署的事,教育部、國防部、內政部、環保署都必須參加。這也不僅僅是中央政府的事,地方政府也一定要能密切配合。這個指揮中心不僅將可以代表政府發言,也是一切問題的單一窗口,各個政府單位如有問題,應該是直接找這個指揮中心,這個中心的另一功能是使中央和地方成為一體,地方上的問題,中央可以知道。
關於SARS管理資訊系統,有絕對建立的必要,任何指揮,都必須先有足夠的資料,……這種系統,不僅僅是儲存資料而已,也是幫助政府做決策的工具,病人要轉診,這個系統會先告知應該轉診的那一家醫院,最為恰當。轉診成功,系統可以立即更新資料。SARS病人去世,系統會替他選擇一家火葬場。並不是每一家醫院都可以治療SARS病人的,也不是每一家火葬場都能執行SARS病人火葬的。
最後,我懇切希望政府能制定出非常詳細而周密的標準作業程序(SOP),以居家隔離為例,這個程序一定要包含誰有權可以發出這個命令?命令如何送達這個人手中?何時生效
?他如何回家?如果有SARS現象,他如何去就醫?(總不能又坐公車去看病吧!)隔離通知書副本該送給誰等等,如果這些細節不在SO P中,我們就有大麻煩了。
六年後,我沒法把自己的憂慮和認為說明得像李先生這麼清楚,但是以我不過從臨時讀來的一些防疫資料所知的來看,相信這麼做是有充分的理由的。以美國這個各州如此重視自己權利的國家而言,碰上防疫的事情,是讓給聯邦的層次來做的。就台灣這樣一個防疫歷史與文化都不足的社會而言,起碼在救急的層面上應該立即做這件事情。
寫這篇文章,也是不想未來六年裡面,再為一個縈繞不去的問題而困惑──並且在一個後果可能更嚴重的環境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