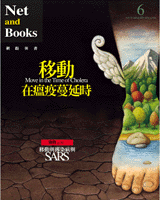From Rex 台北到法蘭克福這一段,機場、機上杯弓蛇影,口罩、手套隨處可見。法蘭克福到馬德里那一段,少了對傳染病的恐懼,卻多了因應恐怖份子的重重關卡。機場除了正常的安檢外,西班牙的櫃台因為支持美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又多了額外的戒備、搜身。草木皆兵。 歸納一下,真是SARS in the East, WARS in the West. ◎ 那時柏林圍林圍牆剛倒。一路上到處是歡欣的氣氛,好一個昇平時代。 的確。人類幾百萬年歷史下來,大約一百多年前終於發明出各種劃時代的陸上、水上、空中交通工具,才剛要享受一些移動的快感,不旋踵就為幾場重大的戰爭加上幾種重大的政治意態所阻隔,難以盡情馳騁。德國統一象徵的冷戰結束之後,所有的移動才真正進入期盼已久的全球化。 1990年還不只這件事情。那年,提姆柏納李還寫出HTML語言,創造了http程式碼,以及World Wide Web的瀏覽器軟體,把事實上已經存在了三十年的網路與電郵,普及到全世界每個角落。人類的移動,不只在真實世界裡無拘無束,甚至進入到虛擬的空間。 1990年代,不真是人類移動得最自在又快活的一個階段嗎? ◎ 以前,出門、出差、旅行、遷徙、漫遊、流浪、朝聖、移民這些種種不同的移動方式,名稱不同,定義不同,性質也不同。但1990年代之後,這些移動方式的界限卻開始改變與泯沒;移動的起點與目的地,故鄉與他鄉,家與居處,也都跟著開始產生本質上的混合。 我們在這些界限的泯沒與混合中享受著方便,偶爾對感受到的不適吐露一些抱怨──其中還可能夾雜著某種難以言說的飄飄然。
2003年4月,SARS 和WARS的雙胞胎,只是現實送來的兩個使者──帶著要我們重新思考移動本質的訊息。 ◎ 因此,我們要想沒有戰爭,或者,沒有傳染病,就必須重新思考移動──移動的本質、方式,及目的。 ◎ ◎ ◎ 《易經》的思想裡,宇宙萬事萬物莫不時時刻刻而在變易,因此只有相對而沒有絕對的動靜。佛教東來之後,「雖動常寂,故曰無為。雖寂常動,故無不為也」(元康《肇論疏》),仍然是同一個概念。就算不拘一格的莊子,一方面說「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也」,是對不停的移動的反思,但是他也說「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蹍而後善博也」,還是肯定人總要一步步跨出去。 中國文化裡,對動靜──移動與停止,是有一套自己的思路的。只是這套思路在近代,由於主客觀的形勢,讓步於西方擴張型的移動思路。 ◎ |
|
|||||||||||||||||||||||||||
| Copyright
2001, 2002, 2003 Net and Book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