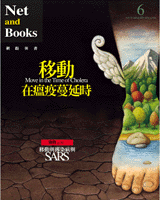流徙之戰 張大春 我還沒讀完這一篇短短的列傳,幾乎就已經可以確認:王克純教授之所以引用阮葵生《茶餘客話補編》這一段文字的用意了。他其實並不希望我再從曹植個人的生平和情感去理解一個曾經遭到放逐的文學家究竟是「秋蓬惡本根」?還是「願與根荄連」? 反倒是陸佃──比起鼎鼎大名的曹植來,這個在宏觀的歷史地圖上幾乎令人無從檢索的小人物──給了我一個非常不同的理解角度:蓬草之所以會遇風拔旋、離棄本根,乃是因為它本來就必須透過遷徙才能存活。從一個比較抽象的理解層次來說:陸佃也必須背離他的老師王安石,才能真正發揮出由王安石所傳授的經術奧義。更激進地看:如果不能疏離整個時代運行的軌跡,蓬草一般的知識官僚便也無從彰顯他們在封建帝王所操控的機器裡容身的價值。甚至──非常諷刺地──他們必須流徙,才算安身立命。 陸佃本人生平行事其實成為一個有力的佐證,使「蓬」這種植物在文學中喚起的意象有了十分重大的開拓。蓬草不再是因風飄盪、隨時俯仰,且除了感慨失根、怨嘆懷舊之外,別無情感深度的感傷符號。從另一方面來看:「蓬葉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雖轉徙無常,其相遇往往而有,故字從逢。」反倒像是是在鼓舞著那些因為見解不合時宜、議論不入時聽,政爭失敗、志氣沮喪,乃至於流徙、放逐的士大夫們:「人生何處不相逢!」 更可貴的,陸佃對於「蓬」的期許,似乎也超越了門第、超越了黨派。你彷彿能夠在這短短的一小段話裡感受到,他那「相遇往往而有」所形容的,既非新黨、也非舊黨;既非熙寧、亦非元祐。「轉徙無常」一語也絲毫沒有悲憐挫辱的情懷,反而給人一種兼容並蓄的寬大之感。質言之:陸佃似乎就是一棵在翻雲覆雨的風潮中飄颻到最遠處、卻仍向一群無論敵友、但凡值得敬惜之人道一聲「珍重」的蓬草。 然而,這還祇是我的對手這一步棋的一半而已。他為甚麼會貿貿然提出這麼一句:「祇不過阮公對於檳榔的厭惡,大概會讓很多流徙者的後代十分不爽罷?」仍舊須要進一步耙梳。 其實,這兩句話可以說是天外飛來,讓我模模糊糊想到了甚麼,可又怎麼也想不起來:它究竟與一樁甚麼事有關?結果在書房裡踱了半個多小時,鬼使神差一低頭,看見我拿來墊垃圾桶底的報紙上有那麼一則算是「消息」的東西。 四月十七日《聯合報》的專訪,受訪者是中研院史語所學者林富士,標題是〈文人雅士食補 蘇東坡、朱熹也吃檳榔〉。訪問稿中提到:這位叫林富士的學者想要「以通古今之變的目的」寫一本《檳榔文化史》。「寫這樣的題目,當然會觸及台灣的檳榔西施,」這位教授表示:「他不會把檳榔西施看成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現象』。」他還建議:「政府與其取締檳榔西施,不如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 我努力回想著四月十七號那一天,大約就是當我看到了「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一句之後,便把報紙塞進垃圾桶裡去了。 在這裡一定先要說清楚:我其實並不討厭檳榔。以前作電視節目熬夜剪接的時候,還多虧檳榔提神醒腦。我甚至認為:這兩年桃園縣政府大力取締檳榔西施是一種以公權力干犯老百姓生計的勾當。但是,我一聽見「不把檳榔西施看成是『社會問題』,而是『文化現象』」、或者「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種鳥話就泛噁心,這是沒辦法的事。 那麼,我的對手是不是知道我把這張報紙塞進垃圾桶裡呢?在動這個念頭的同時,我忍不住扭頭看了一眼窗外──在我書房的外頭,有一株山櫻、兩棵龍柏和一整排密匝匝的竹子,應該不可能有甚麼人能在任何時候窺看到我塞報紙的那個小動作。那麼,王克純教授為甚麼會在覆手時莫名其妙地來上那麼兩句呢?看來祇有一個可能:他不但希望我注意阮葵生對於「轉蓬」所抱持的態度,甚至也希望我還能理解他對「檳榔」所抱持的態度。 那麼,這個態度跟流徙有關嗎? 關於阮葵生,我所知更少。祇依稀記得:他大約是清乾隆年間的人,做過刑部侍郎的官。此外,我還知道《清史稿•藝文志》有著錄,將阮葵生所寫的十二卷《茶餘客話》歸入子部雜家類雜說之屬。至於《茶餘客話補編》究竟是怎樣的內容?由何人補綴而成?甚麼時候出版?我就一概不明白了。而且,在我們這一場賽局之中,就算知道了也沒甚麼用,因為我的對手已經引用過的書,就是「三不」的禁令之三──「不可以出自同一本書」。然而,我仍忍不住如此想道:他會不會是希望我去翻看一下阮葵生對「檳榔」的看法呢? 我沒見識過那本補編,手頭倒是有一本《茶餘客話》。這一回並不太費力,我很快地就翻檢到〈吃檳榔惡習〉這一條。題已標之為惡,其不屑可知。 「大腹皮,本草言其性罪猛;破氣,虛損者忌之。其子即檳榔,性益加厲,今人多好食之、亦無恙。檳榔樹高五、七尺,皮似青銅,節如竹,其葉聚於杪。業下數房、房結數百子,名『棗子檳榔』。中有實,如雞心,與海南子無異。粵人、滇人熟而後食,台灣人則生時即取食之,云可治瘴氣、消飽脹。以蠣房灰用柑子蜜染紅,合海沼藤食之。每會席,賓客前各置一枚。京師小人和蘇子、荳蔻貯荷包中,竟日口中咀嚼,唇齒搖轉,面目可憎,威靡數十千。近士大夫亦有嗜者。阮亭(按:即王士禛,別號漁洋山人)云:『轎中端坐吃檳榔』,貴人亦不免矣。范石湖云:『巴蜀人好吃生蒜,臭不可近。頃在嶺南,其人好吃檳榔,合蠣灰抹扶留藤,食之則昏、已而醒快。三物合和,唾如膿血,可厭。今來蜀道,又為食蒜者熏,作詩云:『南飧灰薦蠣/巴蜀菜先葷/幸脫蔞藤醉/還遭胡蒜熏。』邱濬贈五羊太守詩云:『階下腥臊堆蜆子/口中膿血吐檳榔。』又《峒溪雜志》載:『蔞藤葉可以做醬。』即蒟醬也。』 初初這樣一讀,我大概可以猜得出:王克純教授也看了四月十七號的那張《聯合報》,大概他也受不了「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這種鳥話罷?那麼,我該附和他嗎?或者──駁斥他? 直覺告訴我:王克純教授想藉由阮葵生對檳榔的厭惡來隱喻一個政治性的態度,那是人類從聚居成部落性的動物之後就再也沒有改變過的一種歧視情感:距離權力核心越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一切就越骯髒、越邪祟、越野蠻。所以無論巴蜀、嶺南或者我們今天定居所在的台灣,看在阮葵生這樣的人的眼裡,其實就是「階下腥臊」、「口中膿血」的符號。 我很快地想到:那位想要「提升檳榔西施的藝術層次,扶植成為文化創意產業」的學者也許並不是一個愚蠢的蛋頭,反而是親切地體認到檳榔──做為一種邊陲賤民的可憎食物──其實祇不過是一個巨大的權力機器咀嚼之後任意唾棄到遠方的一種渣滓罷了。 流徙,於焉不祇是一種懲罰,而簡直是一種罪惡了。 「誰說中國人沒有原罪觀呢?」我在回覆王克純教授的電子郵件上打下了這樣幾個句子:「我們的原罪就是流徙,距離權力越遙遠,中國人的罪孽感就越深重罷?」
|
|
|||||||||||||||||||||||||||
| Copyright
2001, 2002, 2003 Net and Books |
||||||||||||||||||||||||||||